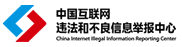桂ICP备11001999号 桂公网安备 45012302000010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4501230001 故障反馈、删帖、纠错投诉,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2014.08.05_F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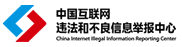
■陆冬琴
“三十的爆竹满地红,初一的新酒散弥香。”乍暖还寒的初春,微风拂面冰凉,却总有些人有些事,可以将冰雪溶化,让心温暖。
晨起时,望见院子里昨儿半夜的满地红,纸屑同露草混在一起,红绿相间分外惹眼。竹叶香扎在门酊上,贴上“利事”、对联、门神,更是喜庆了。小辈们向长辈道贺、讨红包的吉利话在大厅里此起彼伏,嗯,又到春节了。
母亲的果摊总是风雨无阻,大年初一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一片,过年也得做生意,上午九点开门下午三点歇业,历来如此。
去景区必过这一条路,大早上的人还真不少,热热闹闹的邻里街坊一声接一声的“发财”不绝于耳。外边马路上有个阿公摆摊儿,黝黑的雷公脸皱皱巴巴,带顶蓝呢小毡帽,总有些不拘的头发刺出来,像个济公,蓝色解放服打了不少的补丁,是个60年代的村干部了,而卷起的裤脚证明了他潮流教主的地位无疑。乌漆麻黑的台布桌子甚是不吉利,上边儿的水果倒是整整齐齐,麻光透亮。不知道他为什么总弄这些个奇奇怪怪的搞头。
这位阿公可了不得,旁边一起摆摊儿的几位都不大愿意靠近他,总有一股莫名的怪味儿。听那几个阿母讲,这个阿公向来独住,儿子儿媳常年不回,难怪老头子性冷孤僻。村里有个关于他的传说,同桌一块儿斗地主,他放个屁能臭晕一屋子人,自此威震八方,名扬四海,大家也就敬而远之了。
照理儿是下午三点歇业,这一转眼就一点多了。可阿公的摊子摆了整一天也没卖出什么。这不,他可得四处走动走动了,但凡有车停在附近的,阿公都得拿了两把香蕉敲人家窗户,:“小妹、小弟,买把蕉不,靓仔美女吃点果,阿公滴水果甜又亮了喂~”晃晃悠悠来来去去也不见得有人要,他只得又提了回去。有人从车窗里塞出十块钱,果不要,可怜可怜老人。阿公脾气大呢,破口就是:“伢了乖乖,你谁啊!老子要你可怜噢?!”倒弄得人家一脸尴尬,几个阿姆都劝他收了,人家一片好心,阿公偏不,张口又是长篇大论,又是一句“你瞧不起老子!”顽固不化的老古董,拖着步子又慢慢回去。仰天长叹一声,满面神伤。
忽而听得远处一声惊呼:“噫!老阿公,那个莫不是你儿子儿媳妇回来了?!”阿公闻得一阵惊咋,猛地站起,又失望坐下。一看,像是像,可那是刘叔家的小儿子,哪里是他的榆钱。过不久,远远地看见一来人,携妻带子的,噢!榆钱,他家榆钱果真回来了哟!顿时老泪纵横,儿子扛起袋子,拉扯就走:“爸!咱回家吃饭,晚了饭该凉啦。回来晚啦,您老莫生气。”“嗳!”一家老小在春日骄阳里拉着老长的影子慢慢地走慢慢地走.........
阿公的事大概就是这样,又是一年大年初一,瑟瑟寒风里想起去年的这桩旧事,莫名觉着温馨可亲。
“阿公!这么早就收摊儿啦?”“嗳!我儿榆钱他回来啦!”百世人生里,有这样一张憨态可掬的老脸,笑着,竟也觉得莫名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