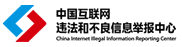桂ICP备11001999号 桂公网安备 45012302000010号 政府网站标识码:4501230001 故障反馈、删帖、纠错投诉,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2014.08.05_F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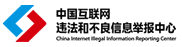
人老了,都喜欢回忆,都喜欢怀旧吧!今天,在这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雨里,我又想起了童年的那一场场春雨,还有那一缕缕弥漫在雨雾里的糯米糍粑的香味。
家乡是水稻区。记忆中的童年,缺的是钱,不缺的是大米、糯米,只是,大米和糯米换不了多少钱。那时候,最盼望的是来一场雨吧,一场大雨。因为,只有在雨天,父亲和母亲才会卸下肩上的扁担、锄头,坐在屋里。父亲修理一些坏了的农具;母亲则开始做糯米糍粑。而我们这些孩子,乐坏了,又有糍粑吃了!没办法,我的童年是一个食物匮乏的童年。
做糯米糍粑的工序不是很复杂,但在小时候,却很费时费力。那时候的碾米房没有安装鼓风机,碾出来的米粒掺着大量的米糠。米碾好之后,母亲得先用较细的筛子“粞筛”,筛下细细碎碎的米糠,再用竹匾“落筛”一遍,才是可以下锅的米。至于做糯米糍粑呢,得先把干净的糯米粒用温水浸泡至变软,然后磨浆,米浆滤水晾成半湿的米团才能捏成型。其实,母亲并不喜欢下厨做糯米糍粑,大概是平时劳作过于疲累,她也想着趁下雨天稍作休憩吧。但拗不过我们几个孩子对糯米糍粑的馋——左邻右舍都在做呢,难道让自家的孩子眼巴巴地馋吗?于是,母亲一边抱怨一边着手准备:筛米,浸米,清洗石磨、细纱布和竹匾。一个时辰之后,用热水浸泡的糯米开始变软。母亲用一个断了柄的箩筐装上大半箩筐的煤炭灰(煤炭灰容易吸水),沿边挖成锅状,铺上半湿的干净的细纱布,再架上石磨架子,架好石磨,开始磨米。我喜欢看着乳白的米浆从石磨里汩汩流出,流进铺着细纱布箩筐的样子,更是因为对糍粑的“馋”,所以每次都舍不得离开石磨半步。母亲便让我跟着她摇磨盘或者往磨盘眼添米。可是,摇了不到半支烟的功夫,我的手臂已经累得不行,添米也跟不上了节奏。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嫌我碍手碍脚,凶巴巴地吆喝着让我走开。而我,嘴里答应着,双腿却挪不开半步。于是,逼仄的厨房里,剁馅儿声,石磨声,母亲的责骂声,响成一片……直到一股掺杂了肉味、蒜味、糯米味的香味儿四下溢出,一切才归于平静。
雨天,除了做糯米糍粑,母亲有时还会蒸米粉:把籼米浸泡、磨浆,柴火旺旺地烧开一大铁锅水,把米浆在编织得细细密密的涂抹了一层花生油的竹匾里薄薄地浇上一层,放到铁锅上的蒸架,盖好竹盖子……火焰熊熊舔着锅底,沸水在锅里“咕噜咕噜”地翻滚,一股清新的香味钻出厨房,是竹香味儿也是米香味儿,飘进雨雾,暖暖的,甜甜的——一条米粉已经蒸熟……前几年,为了寻找儿时的这股米粉香味儿,不惜几次驱车到邻县的某一饭店,只为饭店里的那一碟米粉皮,有着竹香味儿和大米味儿的米粉皮——吃的是一碟粉皮,忆的是渐行渐远的童年,念的是渐渐年迈的双亲啊!
岁月从不轻饶任何人。双亲渐老,我也不再年轻,但过去的一些时光并未随着鬓角灰白而变淡,倒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于是,在这个春雨里,我买了现成的糯米粉,精心剁了馅儿,做了十几个糯米糍粑。然而,孩子并不喜欢吃。